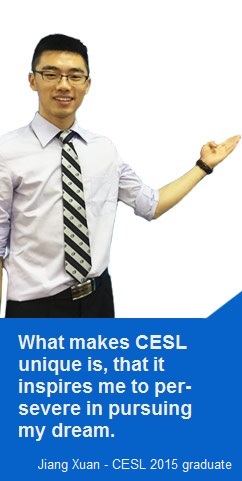2018年9月27日,中国政法大学中欧法学院2018年博士生交叉法学集体指导课第五次讨论在国际交流中心第二会议室举行。此次讨论课邀请到《环球法律评论》杂志副主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支振锋和北京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所长张真理两位嘉宾参加。本次讨论由中欧法学院郑永流教授主持,中欧法学院博士研究生谭伟杰作主报告,中欧法学院赵天书博士与2018级博士研究生李丹华、杨阳、陈鲁夏及海南大学法学院许少芬参与讨论。本次讨论课的阅读材料为扬·斯密茨《法学的观念与方法》中的前言和第一章,内容为传统法学的危机、传统法学身份认同的危机以及四种类型的法学研究等问题。
读书之道
讨论伊始,郑永流便向参与人分享了读书之道。他指出,在阅读过程中我们应该始终带着这样三个问题:首先,作者说了些什么?其次,作者说的怎么样?再次,我该如何继续说?本书的前言一直在强调传统法学的危机问题,那我们首先应该问,作者在这里所强调的传统法学的危机以及传统法学的身份认同危机到底有何指涉?
传统法学的危机
杨阳结合本书中所引用的冯·基尔希曼的观点,认为法学这种偶然的东西是根基不稳的,故而法学需要建立自己的体系、自己的研究范式以找到它自身的确定性。但之后,法学又面临着理论与实践的冲突问题,传统法学教义式的内部分析视角无法为法学找到正当性论证,法学需要从其他学科那里寻求价值依托。但与此同时,其他学科的价值观和研究方法却反客为主不断侵蚀着传统法学辛苦建立起来的领地。因而,传统法学的危机在于缺乏体系性,而当下传统法学所面临的身份认同危机则来自于其他野心勃勃的学科对法学的挤压。郑永流赞同杨阳的说法,认为法学的危机在于缺少对法律正当性的证成,而这只能从法学学科外部着手。
李丹华提及波斯纳在其著作《各行其是》中探讨的理论和现实脱节的问题,并认为法学院或法教义学能做的似乎只是传道与授业,但它们无法及时地对法学的实践予以解惑。
张真理认为我们首先要理清这样几个问题:首先,这场危机、这场冲突发生在谁和谁之间?其次,这种冲突性质如何?再次,我们该怎么解决这种冲突?概括而言,法学经历了一个从没有体系到有体系,再从有体系到面临理论和实践各行其是的困境。
四种类型的法学研究
接下来,谭伟杰向大家报告了作者在书中所提到的法学研究的四种类型,这四种类型分别回应了四个问题:描述性法学回应了如何阐释法律的问题、规范性法学回应了应当如何阐释法律的问题、实证性法学回应了适用某种法律规则会带来什么样的后果的问题,理论性研究回应了法律是什么的问题。其中,作者又把描述性法学分为四种,即法律的社会学描述、法律的经济学描述、法律的历史学描述以及法律的比较学描述。
郑永流请大家结合书中两个地方来理解描述性法学,一个是在酒吧破产案件中,法学家将酒吧的高脚凳界定为动产还是不动产,这直接决定着高脚凳最终的所有权归属;此外,我们该如何理解“‘我们如何思考法律’与‘我们所思考的法律’并非两件不同的事情:‘定义创造了现实,就像前者安排后者那般”这句话。
赵天书指出,如凯尔森所言,实在法兼有实然性和应然性,它的应然性表现为它是我们观念中的世界,它的实然性表现在它一旦成为实在法就会在真实的世界中发挥作用、产生效用,但这种效用不一定是我们在概念世界中所构想的那种理想状态。如这里对高脚凳定义就会影响到交易成本和社会生活,这就是其实然的一面。所以,描述性性法学还是指法在现实中到底是何种样态、发挥了何种作用以及产生了何种功能。
陈鲁夏指出康德的哥白尼式革命导致了认识论的转向,以前是客体决定主体,康德之后是主体决定客体。也就是说,法律是我们所创设的东西,我们对法律的定义塑造着现实的法律关系。
郑永流用两个命题对此作出了回应。首先,“法律即是法学的对象,也是法学的产品。”也就是说,法学既把法律作为自己的研究对象,同时它又改变着法律、创造着法律。高脚凳是动产还是不动产,这是由我们人为设定的,而不是其本身具有动产或不动产的属性。康德哲学有一种客体的主体化倾向,在诸如法学这样的人文社科领域中,主客体之间的分离是不存在的,客体往往只是主体设定的结果,也就是“定义创造了现实”。比如,我们不能仅就法律教义来理解法律教义,更重要的是,我们对法律的解释本身又成了教义。其次,“法学是一种权力性的知识”。法学创造法律,因而便有了一种立法的权力。而在司法中,法官的工作其实是在不停地造法,法官对法律的认识和解释才是能解决纠纷、对判决有约束力的。也即是说,法官的解释才是判决的真正根据,而这种根据如同法律本身一样具有效力。
张真理认为,郑老师提出的“法学是一种权力性的知识”的命题更多的是关于法学功能的一种描述性概括,也就是书中所说的“法学可以创造法律”,更进一步而言就是法学可以续造法律。续造是建立在既有的法律体系、法律学说之上,然后在具体的法律适用和研究中产生新的规则。比如,以前我们对财产概念的界定都是实体的,但后来出现了电、虚拟财产等,这些属不属于财产概念?也就是说,我们在创造新的财产概念的时候,实在法对之是没有规定的。我们首先要在法学理论中建立起这样的规则,我们认为虚拟财产应该被纳入法律,之后实在法才吸收了这样的概念,这就是法学的一种创造性倾向。法律人要做的就是通过规则指引把生活世界变成了法律世界,法律人的眼中尽是有法律意义的事实。
支振锋认为法学本身有一套复杂的社会机制来对社会问题进行规范性提炼,从而产生新的法律渊源,即法学通过影响它的产律来构建事实与规范之间的链接。其实法学创造法学也只是在启蒙之后才可能,启蒙让人的理性能力得到彰显,法从神的造物变成了人的造物,这也是实证主义法学的贡献。
分类?抑或类型化分析?
郑永流认为作者这里区分四种描述性法学的标准其实是很模糊的。按照作者的分类,我们无法区分法律教义学的描述和法律社会学的描述,也无法区分法律社会学的描述和实证性研究。非教义学有两种功能,一是提供经验的证明,二是提供正当性。在法律的经济学描述中,作者试图用经济学原理为法律提供正当性论证,即试图用经济学的效率原则补充过去以公平为核心的正义价值。这不仅仅是描述,而更多的是一种规范性的研究。
赵天书对此的理解是法律教义学是法的本体,而社会学和经济学是对这种本体的描述,这构成了如郑老师所描述的一阶法和二阶法的关系。郑永流补充到,在一阶法的理由无法完全解释时,需要二阶法的补充,比如需要经济学和哲学知识来证成法律的正当性。
最后,张真理总结了两种清晰呈现文章的方式,一是分类,二是类型化分析。分类有分类的规则,比如子类之间不能相互交叉。而类型化分析也要有规则可循,正如郑老师对法教义学实践面向和非实践面向的区分。而作者在这里提出的四个问题,既不是分类也不是类型化分析,这难免让读者感觉到这四个问题之间的交叉与不完整。比如,作者用法教义学回应如何解释法律的问题,但法教义学既是规范的也是实证的,除了作者提到的法教义学的体系性、系统化和内部的视角之外,法教义学中还应有一种参照事实的视角,这被作者忽略了,从而导致了在描述法教义学特质上的缺失。总之,由于作者提出的作为分类标准的这四个问题之间的交叉与含混,导致了整个分析上的不完整以及四个子项(法学研究类型)内容上的缺失。
Empirical:实证的?抑或经验的?
接下来,谭伟杰对于书中实证性法学的部分继续作报告。他指出,实证概念是容易引起混淆的,法律实证主义,分析实证主义,所谓的实证实在于法律规则。而本书的实证性法学实在于社会事实,即法律事实上如何运作及其所产生的社会效果,它不关注法律规定了什么,因此区别于规范实证。
支振锋指出,通常实证主义对应的是positivism,而empirical显然应该是经验的。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学界开始把empirical翻译成“实证的”,比如书中就把empirical legal scholarship翻译成实证性法学。这样翻译是容易导致混淆的,比如我们无法区分法律实证主义和法的实证性研究。
赵天书认为,实证主义法学源自于凯尔森、哈特等人,他们把法律看作为一个封闭的逻辑结构,主张下位法的效力来自于上位法。而法的实证性研究背后则是一种法律工具主义,当实证性研究直接贯穿到规范性法学中时,当直接从实证性研究中寻找法律的正当性依据时,实证主义法学将被瓦解。这也是实证主义法学和法的实证研究之间的冲突的来源之一。
支振锋认为,法律实证主义其实是一种法哲学,它追问什么是法、法为什么具有规范性、为什么要守法这样的原命题,这是对法的认识问题;而法的实证性研究,或法的经验研究,其实是一种法的经验研究方法,它从法的运行层面来关注法是什么的问题。
郑永流指出,支振锋的意思是法律实证主义和法的实证研究分别回应了本体论和方法论的问题。一般来说,法律实证主义是相对于自然法而言的,自然法从内容上回答了什么是法律的本体论问题,即探讨法律的合理性问题。而在法律实证主义内部还有两派:一是以凯尔森、奥斯丁为代表的规范逻辑的实证主义;二是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法社会学)。这两派对于实证的理解以及对于法律是什么的解读是不同的,在规范逻辑的实证主义那里,实证指涉的是制定法,其认为形式上国家制定的就是法,它关注法律形式的合理性;而在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那里,实证性和有效性是联系在一起的,他们认为实际有效的东西才是法律,它关注法律的实际有效性。所以,自然法、规范逻辑的实证主义和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都试图回答着法律的本体论问题,只不过回答的角度不同,自然法注重法律内容的合理性,规范逻辑的实证主义注重法律形式的合理性,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注重法律的实际有效性。由此,虽然可以区分法律实证主义和法的实证性研究,但不是说它们一个在回答本体的问题,另一个只是在描述。法的实证性研究(或者经验事实的实证主义,或者支振锋所言的法的经验性研究)也不纯然是描述性的、方法论层面的,它也在回答什么是法律的本体论问题。
支振锋指出,以边沁、奥斯丁、哈特为代表的法实证主义关注的是法律本体论问题。后来,埃利希、卢爱林等人从法的功能来理解法,他们也关注法的本体问题,但和法实证主义不同。再后来,法律经济学研究、社会科学理论都是从方法论层次研究法律,这属于经验研究(empirical studies),是一种研究方法。我想强调的是,把empirical翻译成“实证的”是不恰当的。
郑永流认为有几对概念需要理清。首先,自然法和实证法是一对概念,自然法是观念的,制定法是实证的。但是,经验的研究为什么是实证的呢?其实,经验研究和制定法又是一对概念。制定法是law in paper,而这里的实证是law in action,即在现实生活中如何体现实在的事实,实证总是和事实联系在一起。经验研究要做的就是通过经验证明制定法在现实生活中实在的状况。其实,从“实证的”到“经验的”体现了我们认识发展的一个历程,在奥斯丁的时代法学是受自然科学影响的,在自然科学领域存在一个外在的实体,我们可以对之加以观察,所以那时用的是实在的,而不是经验的。但后来,在社会科学中不存在一种外在的实体,而更多是一种可描述的经验。
撰稿:陈鲁夏